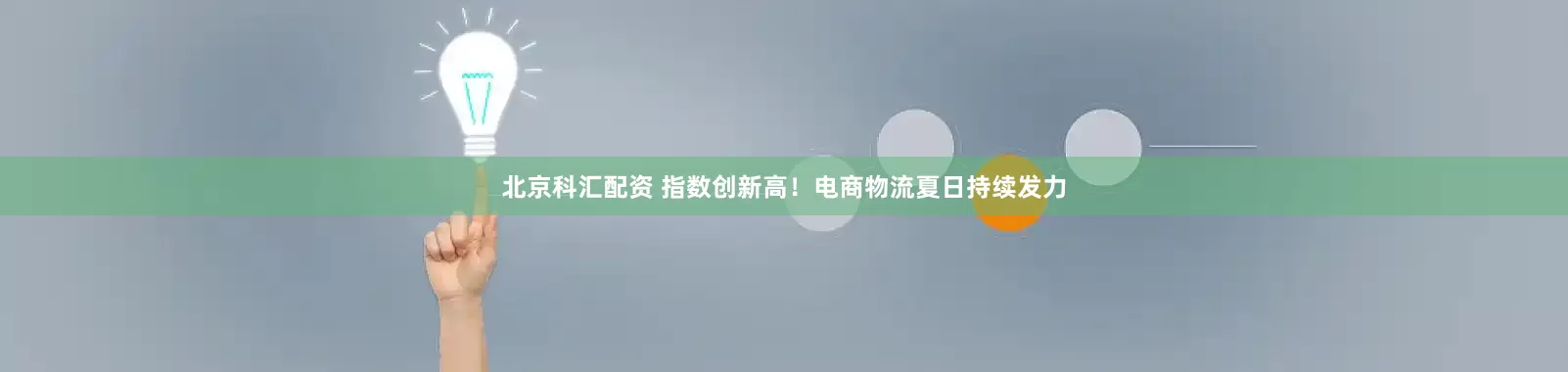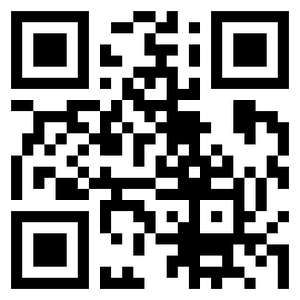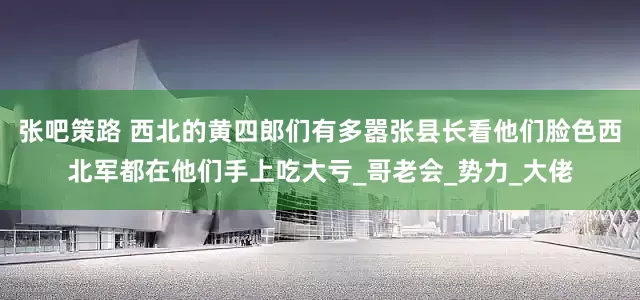
民国时期可谓是一个“大哥遍地走”的时代,黄四郎们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那时的中国,甚至连拥有十万兵力的军阀,都得向黄四郎们低头称“大哥”。例如,韩复榘和蒋鼎文等军政要员都要称张仁奎为“老爷子”。在成都,大多数警察局长都有着与袍哥的千丝万缕联系。对于那个时代的人而言,能够拜黄四郎这样的“大佬”为师,实际上成了一种军事和政治上的保险,几乎成了他们不时走运、避开麻烦的必备法宝。这种情形张吧策路,在西北地区尤为显著,西北的哥老会势力同样也涌现出了不少黄四郎。县长们必须时刻留意黄四郎们的心情,甚至在马家军与西北军的大规模冲突中,也得依赖黄四郎们的立场来决定阵营。
黄四郎在电影中出现在辛亥革命的历史画面中,实际上,西北地区的黄四郎们就是当时反清起义的主力军。西北的同盟会,实际上也不得不对这些哥老会势力屈服。西北的反清起义分为两大阵营,其中复汉系统的反清武装,基本上是同盟会的人马,而洪汉系统则以哥老会为主导,实力庞大。西北地区的哥老会武装明显在两股力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,尤其是在陕西光复后的局势中,虽然只有大统领张云翔是同盟会成员,其他所有的都督和军事领导人几乎都来自哥老会。而且,同盟会为了适应这种情况,只得公开承认“财权和兵权都被哥老会掌控”。
展开剩余73%军政府的命令若没有“洪门会议”标志,就无法生效,意味着陕西几乎成了“洪门的天下”。北洋政府初期,西北地区的军队编制为两个师和四个旅,而哥老会的大佬张云山手中就有一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,另一位重要人物万炳南也有一个旅。整个西北军中,哥老会的势力占据了四分之三之多,足见其影响力之大。
在西北的各大会道门中,哥老会几乎一枝独秀(尽管一贯道等道门势力也有一席之地),甚至青红帮的存在都显得微不足道。以五原县为例,几乎全县九成以上的人口都已经加入了哥老会,而绥远的各县加入哥老会的人口比例从未低于五成。到1936年,甘肃省及甘宁区和甘青区的总人口为884万,而哥老会的成员数量就达到了六七十万,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。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,甘肃省的各个阶层几乎都成了哥老会的一部分,包括农民、工人、商人、军人、教育界人士以及乡镇长官等,足见其在西北地区的深远影响。
民国时期,西北的政界和军界人物往往不如哥老会的黄四郎们来得稳固。甘肃的局势更为复杂,西北军进入甘肃后,残酷镇压了甘肃八个镇守使中的六个,军头们或死或下野。那些失去权力的军事领导人,几乎都成了失势的“凤凰”,不得不依赖哥老会的大佬们来保全自己。
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西北军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势力,然而它与哥老会的冲突几乎是注定的。西北军进入西北后,实施了针对支持哥老会的土匪的剿灭政策,并且重创了与哥老会有着紧密关系的本地军头,这使得西北军和哥老会的矛盾愈加深刻。此外,西北军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,甚至在西北地区大幅度提高了税收,这使得大量西北农民转而加入哥老会,甘肃省的农民加入哥老会的数量竟达到六七十万之众。哥老会的势力之庞大,甚至让冯玉祥不得不公开承认其为革命协会,并亲自拜见了哥老会大佬马福元,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西北的地位。
哥老会作为地方势力的霸主,表面上与西北军保持了臣服关系,但在马仲英与西北军对抗时,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。马仲英虽然是马家军的成员,但他不拘泥于家族信仰,主动在甘州开设了高台山山堂,并利用哥老会的势力招募兵员。此外,马步青的第一师师长马呈祥自称为“中华山副山主”,而马步芳手下的韩起功旅也有大量成员加入了哥老会,甚至马家军的民团动员也都依赖哥老会的力量。
尽管哥老会内部分子复杂,有一部分人支持进步力量,但整体上它依然是一个深深植根于地方的庞大势力。西北的哥老会黄四郎们在那个动荡年代,统治了西北多年,成为了西北一大“毒瘤”张吧策路,影响深远且难以撼动。
发布于:天津市东方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